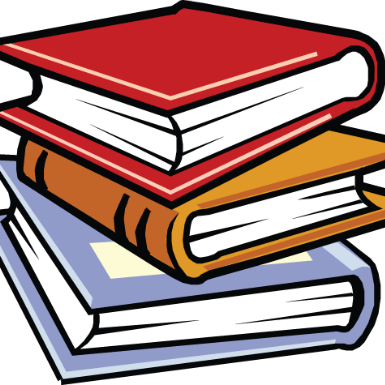“好像耶稣踩水走到船上一样!”
“有时候是,”他说,“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他看上去很伤心和疏远,我又感到有点儿害怕,但也为他难过。不过我完全不知道他难过什么,他车库里有太平湖这么棒的模型世界,还有什么好难过的。
“这实在是个很精彩的把戏。”我说道,我拍拍他肩膀。
他回过神来,朝我咧嘴一笑。“你说得对,”他说道,“我觉得我大概是想念我的妻子和儿子了。杰米,我觉得这就是我要把你从你妈那儿借过来的原因。不过我现在得把你还回去了。”
当我们回到9号公路时,他再次牵起我的手,虽然两边都没有车,但我们还是这样手牵手一直走上卫理公会路。我不介意,我喜欢牵着他的手。我知道他是为我好。
雅各布斯太太和莫里几天后到了。莫里只是个穿着尿片的小不点儿,但雅各布斯太太好漂亮。周六那天,就是雅各布斯牧师在我们教堂登上讲道台的前一天,特里、阿康和我帮他把太平湖搬到了教堂地下室,卫理公会青少年团契每周四晚会在那里开。水抽干之后,湖泊之浅和穿过湖底的那道槽都非常明显。
雅各布斯牧师让特里和阿康发誓保密,因为他不希望这个幻象在小家伙面前拆穿(显得我好像是大人一样,这种感觉让我很得意)。他们同意了,我不认为他们之中有人泄密,不过教堂地下室的光比牧师宅邸车库里明亮多了,只要你凑近去看,就能发现太平湖只是一个很宽的水洼,连有槽轨道都能看见。到了圣诞节,人人都知道了。
“就是个骗人老把戏。”有一个周四下午,比利·帕克特这样跟我说。他和他兄弟罗尼都讨厌周四补习班,不过被妈妈逼着去。“他要是再耍那个把戏,再讲那个水上漂的故事,我就得吐了。”
我想过因为这事儿跟他吵一架,但他比我壮,而且是我的朋友。何况他说的也没错。
II 三年/康拉德的嗓子/一个奇迹
雅各布斯牧师被解雇了,原因是他在1965年11月21日的那次上台布道。在互联网上一下就能查到,因为我有个“记忆地标”:那是感恩节前的星期天。一周后他就从我们的生命中消失了,而且是独自离去。帕齐和莫里——青少年团契的孩子们都管他叫“小跟班”莫里——那时已经不在了。那辆自动挡老爷车也不在了。
从初次见到太平湖到骇人的布道之间的那三年,我印象出奇地清晰,不过下笔之前,我也以为自己记得甚少。毕竟说回来,有多少人能记得自己六岁到九岁之间发生的任何大事小情呢?写作这件事既美妙又可怕,它可以打开之前被盖住的记忆深井。
我觉得我简直可以把原先想写的放在一边,光是那些年和那个世界就足够我写满一本书,而且是一本不小的书,那个世界跟我现在所生活的世界太不一样了。我能记起我的母亲穿着睡裙站在熨衣板前,在清晨的阳光下明艳不可方物。我能记起我那件松松垮垮的泳衣,不起眼的橄榄绿,还有在哈利家的池塘里跟哥哥们一起游泳。我们老说那黏糊糊的池底全是牛粪,不过其实只是泥巴(很可能只是泥巴)。我能记起那些昏昏欲睡的下午,在那所只有一间教室的西哈洛学校中度过,穿着冬装坐在“识字角”,努力让那傻兮兮的迪基·奥斯古德学会拼写“长颈鹿”这个词。我甚至还记得他说:“为、为、为什么要我学、学、学写我永远不可能见到的东西?”
我能记起那一条条的土路像蜘蛛网一样在我们的镇上交错纵横,记得在严寒4月天的课间时分在操场上打弹珠,记得我躺在床上,祷告完毕等待入睡时,风在松林间发出的声响。我能记起我的父亲手持扳手从车库走出来,那顶“莫顿燃油”帽子在前额上压得很低,血从他满是油污的指关节渗出来。我能记起看肯·麦肯齐在《强力90秀》上介绍大力水手卜派,记得克莱尔和她的朋友下午在家的时候,霸占我的电视去看《美国舞台》,想看那些女生都穿什么。我记得落日就像父亲指关节上的血那么红,现在一想起就不寒而栗。
我能记起上千件往事,大多都是好事,但我坐在电脑前不是为了带着浪漫的情怀缅怀过去的。选择性记忆是老年人的主要缺点之一,我没有这个时间。记得的也并不都是好事。我们住在乡下,那时候乡村条件是很苦的。我估计现在依然如此。
我的朋友阿尔·诺尔斯的左手卡进了他爸的土豆筛选器里,他爸还没来得及把那倔强又危险的东西关掉,他就已经没了三根手指。我那天就在场,还记得传送带是怎么变红的,也记得阿尔叫得有多惨烈。
我爸(还有他那忠实又没脑子的助手特里)把“公路火箭”修好了——天哪,引擎运转起来发出的轰响真是帅呆了!他把车子交给杜安·罗比肖,车身刚刚刷好漆,还在一侧饰上了醒目的数字19,要在罗克堡赛道上比赛。在第一轮正式赛的第一圈,这个白痴就翻了车,车子直接报废。杜安下车毫发无损。“那个傻帽儿油门踏板卡住了。”他边说边龇牙傻笑,我爸说,唯一的傻帽儿就是方向盘后面那个。
“吃教训了吧,看你还敢不敢把贵重东西托付给姓罗比肖的。”妈妈说道,爸爸双手插进裤兜,一直用力往里揣,连内裤边都露出来了,大概是为了确保拳头别从裤兜里出来,打到不该打的地方。
莱尼·麦金托什,邮递员的儿子,弯下腰去看他搁进空菠萝罐头盒里的樱桃爆竹为什么没爆响,结果失去了一只眼睛。
我哥哥康拉德失声了。
所以说,不,过去的不都是好事。
雅各布斯牧师上讲道台的第一个星期六,到场的人数非常可观,人数比那胖乎乎、白头发的善心老头儿拉图雷先生开教堂的所有年份加起来都多。拉图雷先生虽然用心良苦,但布道却不知所云,一到母亲节必定双眼含泪,他管母亲节叫母亲礼拜天(这些细节都是我妈妈许多年后告诉我的——我压根儿记不得拉图雷先生了)。原定有20个信众要来,结果这个数字轻轻松松增长了4倍,我还记得在《三一颂》中他们的声音何其激昂:赞美上主,万福之本,天下万民,天上万军。听得我直起鸡皮疙瘩。雅各布斯太太在脚踏风琴上也绝无懈怠,她的一头金发用一条朴素的黑色缎带束在后面,光线穿过教堂唯一一扇琉璃窗,打在她的秀发上,闪耀出万般色彩。
全家礼拜完了往家走,我们留到礼拜日才穿的好鞋子踢着地上的尘土,我刚好紧随爸妈身后,听到妈妈对新牧师表示赞许。她同时也如释重负。“我还以为他这么年轻,肯定会跟我们大讲公民权利,废止征兵一类的东西,”她说道,“相反,他给我上了基于《圣经》的一堂好课。我猜大家会再来的,你说是不?”
“会再来几次吧。”爸爸说。
她说:“噢,你个燃油大亨,还是个调侃大师。”然后娇嗔地打他的胳膊。
事实证明,他们各对了一半儿。我们教会的出席率从未跌回到拉图雷先生当时的水平——他那时到了冬季就不足12个人(在那透风教堂里围坐在柴炉子前取暖)——但人数还是缓缓下降到60,然后50,最后到了40多,就在那附近上下徘徊,就像6月天里的晴雨表。没有人把人数缩减归咎于雅各布斯先生的讲道,他的讲道清楚、动听,不脱离《圣经》(从来不提什么原子弹或是自由大游行一类让人不安的事情);只是大家慢慢游离了而已。
“现如今上帝对大家来说没那么重要了,”在一次出席率尤其糟糕的礼拜后,妈妈这样说道,“他们迟早会为此感到后悔。”
那三年里,卫理公会青少年团契也有了适度的复兴。在拉图雷时代,周四晚上很少有超过12个孩子的,而且其中还必有四个姓莫顿:克莱尔、安迪、阿康和特里。在拉图雷时代,我年纪太小不得参加,就因为这个安迪有时候用拳头揉我的脑袋,管我叫“幸运小鸭”。有一次我问特里那时候的团契是什么样子,他百无聊赖地耸耸肩,“我们唱唱歌,查查经,然后承诺绝不吸烟喝酒。然后他叫我们爱自己的母亲,说什么天主教徒都得下地狱,因为他们搞偶像崇拜,犹太人贪财。还说如果有朋友讲黄色笑话,要想象耶稣就在旁边听着。”
不过在新人领导下,6岁到17岁小孩儿的出勤数暴涨到三十五六个,以至于需要为教堂地下室加购折叠椅。这不是因为有雅各布斯牧师的机械耶稣横跨太平湖;那股新鲜劲儿很快就消退了,连我也一样。我觉得跟他挂在墙上的《圣地》也没什么关系。
主要是他的青春和激情。除了布道还有游戏和户外活动,因为正如他频繁指出的,耶稣的大多数传道都在户外进行,也是表明基督教不止于教堂之内。查经活动依然存在,不过我们是在玩抢座位游戏中进行的,常常是有人摔倒地上时还在找《申命记》第14章第9节或《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2节,挺搞笑的。然后就是打棒球或垒球用的球垒,这是阿康和安迪以前帮他布置的。在某些星期四里,男生打棒球,女生来为男生打气;隔周的周四,女生打垒球,男生(暗暗希望有些女生会忘记晚上要打球结果穿了裙子)来为她们加油。
雅各布斯牧师对电的个人兴趣总能在他周四晚的“青少年讲座”中占一席之地。我记得有天下午,他给我们家打电话,让安迪周四晚上穿一件毛衣来。大家集合后,他把安迪叫到房间前面来,说他想给大家示范一下罪孽的负担。“安迪,虽然我确信你算不得什么罪人……”他补充说。
我哥哥紧张地微笑一下,没说什么。
“也不是要吓唬你们这些孩子,”他说,“有些牧师信这套,但我不信。只是想让你们了解一下。”(后来我才知道,大家都喜欢先说这种话,然后把你吓得屁滚尿流。)
他吹大了几个气球,让我们想象每个球大概20磅重。他托起第一个气球,说:“这个是谎言。”他把气球在衬衫上快速擦了几下,然后把球抵在安迪的毛衣上,球居然就像上了胶水一样粘在上面。
“这个是偷窃。”他又粘了一个气球到安迪的毛衣上。
“这个是愤怒。”
我不太肯定,不过他好像往安迪那件家里缝的驯鹿图案的毛衣上一共粘了七个气球,七宗罪一宗一个。
“加起来就超过100磅了,”他说,“这可是沉重的负担啊!不过谁会带走世人的罪?”
“耶稣!”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没错。当你向他请求宽恕的时候,就会这样。”他拿出一个大头针,把气球一个一个戳破,包括自己跑掉后来牧师重新粘回安迪身上那个。我们都觉得戳爆气球的部分比被神圣化的静电部分刺激多了。
他最了不起的电力示范是他的其中一项发明,他称之为“雅各的梯子”。那是一个跟我装玩具兵的军用手提箱差不多大的金属盒子。上面有两根电线伸出来,就像电视天线一样。等他插电(这项发明需要接电源而非用电池)然后打开侧边的开关后,亮得让人无法直视的长长的火花就会顺着电线往上爬,到顶之后就消失。当他往设备上撒过某种粉末后,一路往上爬的火花就会变成其他颜色,弄得女生们兴奋得哇哇叫。
这还有某种宗教寓意的——至少在查尔斯·雅各布斯看来是这样的——不过我要是还记得的话,那就见鬼了。可能是三位一体之类的?当雅各的梯子不在眼前,没有彩色的火花往上爬,没有电流嘶嘶声像野猫乱叫的时候,这种外来的概念往往就像一场短暂的发烧一样渐渐消逝。
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的一次微型演讲。他对着椅背反坐,以便面对我们。他的妻子坐在他身后的钢琴凳上,双手叠起来端庄地放在膝上,微微低头。可能她是在祷告,也可能她是觉得闷了。我知道很多听众都是闷了;到这会儿,大多数的哈洛卫理公会青少年已经对电及其伴随的荣耀感到厌烦。
“孩子们,科学告诉我们,电流就是带电原子微粒——电子的移动。电子移动,产生电流,电子流动越快,电压就越高。这就是科学,科学是好的,但是科学却是有限的。总有知识到不了的地方。到底什么是电子?科学家们会说,就是带电的原子。好吧,话是不错,那什么是原子呢?”
他向前靠在椅背上,他蓝色的双眼(看上去好像带电)盯着我们看。
“没人真正了解!这时候就需要宗教了。上帝有很多门户通往无限,而电是其中一种。”
“他要是能搞张电椅,电死几只白老鼠就好了,”有天晚上祝祷之后,比利·帕克特抱怨说,“那一定很有趣。”
虽然他翻来覆去(而且越来越无聊)地讲神圣的电压,我们大多数人还是期待周四补习班。当雅各布斯牧师不谈自己的喜好时,他会活灵活现地讲一些从《圣经》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有时还挺逗乐的。他会谈我们面对的真实问题,从欺凌弱小,到考试前没准备考场上想偷看的问题。我们爱玩游戏,大多数的课还是爱听的,还爱唱歌,因为雅各布斯太太弹得一手好钢琴,赞美诗弹得很动听。
她懂的还不只赞美诗。在一个让人永生难忘的夜里,她演奏了披头士乐队的三首歌,我们跟着一起唱了《从我到你》《他爱你》和《我想握住你的手》。妈妈说帕齐钢琴弹得比拉图雷先生要好70倍,当牧师的年轻太太请求用教会募款,从波特兰请一位钢琴调音师上门时,执事们一致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