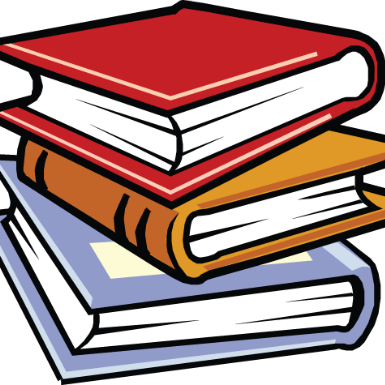第7节
“滚!”她吼道。阿康就是这么冲我吼的,如果他的嗓子还灵的话。“上帝最恨偷听的人!”
她哭了起来。我跑出门,自己也哭了。我沿着卫理公会丘往下跑,跑过9号公路,完全没看任何一个方向的车辆。我没打算去牧师宅邸;我心烦意乱,都没想到去找牧师。要不是帕特里夏·雅各布斯刚好在前院查看花草,看看去年冬天种下的花儿要开了没有,我可能会一直跑到我倒下为止。不过刚好她在外头,还喊了我的名字。我内心有一部分想不管不顾继续跑,不过——正如我前面所说——我是有礼貌的孩子,难过的时候也不能失了礼数。于是我停下脚步。
她来到我跟前,我还低着头在喘气。“怎么了,杰米?”
我没说话。她托着我的下巴,把我的头抬起来。我看到莫里正坐在牧师宅邸前面门廊边的草坪上,四周是他的玩具小卡车。他瞪大眼睛看着我。
“杰米?告诉我出什么事儿了。”
爸妈教会我们做人要讲礼貌,也教会我们家丑不可外扬。旧式美国佬的做派。不过她的善良让我完全敞开心扉,一下子全说了出来:阿康的苦楚(我相信虽然爸妈非常忧心,但他们谁都无法真正理解),妈妈担心他的声带撕裂,再也无法开口说话,她坚持要找专家看看,但爸爸说家里没钱。还有就是我被吼了。我没跟帕齐说妈妈的声音像换了个人似的,但只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表述。
等我终于讲完,她说:“到后面库房来。你来跟查理说说。”
老爷车现在妥当地停进了车库,屋后的库房就成了雅各布斯的工作室。帕齐给我开门的时候,牧师正在鼓捣一台没有屏幕的电视机。
“等我把这宝贝组装回去,”他边说边搂着我肩膀,从裤子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我就能收到迈阿密、芝加哥和洛杉矶的电视台了。杰米,先擦擦眼睛,把鼻子也擤擤。”
我一边擦脸一边惊奇地看着那台没有眼睛的电视机。“你真能收到芝加哥和洛杉矶的电视台?”
“哪能啊,我开玩笑的。我只是想加装一个信号放大器,好收到8号台之外的台。”
“我们家还有6号台和13号台,”我说,“不过6号台老有雪花。”
“你们家用的是屋顶天线。我们家只能凑合着用兔耳朵室内天线了。”
“为什么不买一个?罗克堡的西部车配件就有的卖。”
他咧嘴一笑。“这主意真棒!那我就在季度会议上,跟所有执事说我想花一点儿募款来买电视天线,好让我们家莫里看上《强力90秀》,而我老婆和我也能每周四晚看《衬裙交叉点》。还是算了吧,杰米,跟我说说你怎么搞得这么狼狈。”
我四处张望看看雅各布斯太太在不在,指望她能转述免得我同一件事讲两次,不过她已经悄悄走了。他握住我的肩膀,把我领到锯木架前。我刚好够高能坐上去。
“是阿康的事儿吗?”
他当然猜得到;那年春天每周四晚聚会的结束祷告时,我们都花一部分时间祈求康拉德能重新发生声音,还有为其他受苦的团契青少年祷告(最常见的是断胳膊断腿,其他的还有博比·安德伍德被烧伤,卡丽·道蒂被迫剃光头用醋洗头,因为她妈发现自家小姑娘头皮上长虱子之后被吓得不行)。不过,跟他妻子一样,雅各布斯牧师并不知道康拉德有多苦,也不知道他的痛苦如何像病菌一样在我们全家蔓延。
“爸爸去年夏天买下了希兰燃油。”我又开始哽咽。我真痛恨自己,小孩子才哭呢,但我就是忍不住。“他说价钱太好了,拒绝说不过去,可是接着就来了场暖冬,取暖燃油价格跌到15美分一加仑,现在他们看不起专家门诊了,你要是能听到我妈说话的语气就知道了,她简直像变了一个人,我爸有时候把手插进裤兜里,因为……”不过旧式美国佬的克制又占了上风,我收住了嘴,“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又把手绢递给我,等我擦脸的时候,他从工作台上拿起一个金属盒子。电线从四面八方伸出来,就像一个剪得很糟糕的发型。
“看看这个放大器,”他说道,“正是在下发明的。等我把它接好之后,我会通一根线到窗外,一直通到屋檐下。然后我会接上……那个。”他指着角落里一个钉耙,杆子撑地,锈迹斑斑的耙钉向外伸着。“雅各布斯自制天线。”
“能行吗?”我问道。
“不知道。我看行。不过就算能行,我看电视天线的日子也快到头了。再过10年,电视信号会通过电话线来传播,到时候会远不止三个频道。到了1990年左右,信号就会通过卫星照射下来。我知道这听着像科幻小说,不过这种技术已经存在。”
他脸上有种梦幻的表情,我还以为,这家伙已经把康拉德的事儿全给忘了,但我这才知道他并没有忘。他只是给我一些时间恢复镇定,也可能是给他自己一点儿时间来思考。
“人们起初会很惊讶,然后就会习以为常。他们会说‘噢,对,不就是电话电视嘛’或者‘我们是有地球卫星电视’,不过他们错了。这全是电的馈赠,电已经如此普通,无处不在,竟使得大家都忽视了它。人们会说‘什么什么就像客厅里的大象’,意思是说某样东西太过巨大不容忽视,不过如果它在客厅里待得够久,你连大象都能照样无视。”
“除了你给大象捡屎的时候。”我说。
这让他大笑不已,我也跟着笑起来,虽然我的双眼还肿着。
他走到窗边往外看。他双手叉腰,久久不语。然后转身对我说:“你今晚把阿康带到牧师宅邸来。能做到吗?”
“能。”我回答说,但并没有什么热情。我以为他又打算祈祷,我知道这也无妨,不过为康拉德做的祈祷已经够多了,而且也没见有用。
爸妈对我们去牧师宅邸并不反对(我必须各问一遍,因为他们当晚互不说话了),倒是我花了好大功夫来说服阿康,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也没什么把握。不过因为我答应了牧师,所以没有放弃。我搬来克莱尔当救兵。她对祈祷之力的信念远胜于我,而且她自有本事。我猜是因为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儿。莫顿家四兄弟里,只有安迪与她年龄相仿,能够抵抗她撒娇时的柔情眼神。
我们三人穿过9号公路时,一轮升起的圆月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康拉德那年刚13岁,黑头发,瘦长身材,穿着安迪穿剩下的褪色彩格夹克,手里拿着他寸步不离的记事本。他边走边在上面写,所以字迹参差不齐。“这很白痴。”
“或许是吧,”克莱尔说,“不过我们有曲奇饼吃。雅各布斯太太每次都给我们曲奇饼。”
还有莫里陪着我们,他现在五岁了,穿着睡衣准备上床睡觉。他径直跑向阿康,扑到他怀里。“还是不能说话?”莫里问道。
阿康摇了摇头。
“我爸爸会把你治好的,”他说,“他整个下午都在努力。”然后他朝我姐姐伸出双手。“抱抱我,克莱尔,抱抱我,亲爱的,我要亲亲你!”她从阿康怀里接过莫里,笑了起来。
雅各布斯牧师在库房里,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一件毛衣。角落里有台电热器,电阻丝烧得发红,但工作室里却仍然很冷。我猜他是忙于鼓捣他的各种项目而没有精力给库房做防寒遮罩。那台暂时没有屏幕的电视现在已经蒙上了搬家用的罩子。
雅各布斯拥抱了克莱尔,亲吻了她的脸颊,然后跟康拉德握了握手,康拉德还拿着他的记事本,在新的一页上写着“又要祷告是吧”。
我觉得这有点儿无礼,从克莱尔皱着的眉头我看得出她也这么认为,不过雅各布斯只是微笑了一下。“后面可能有,不过我们先试点儿别的。”他转过脸对着我,“天助何人,杰米?”
“自助者天助之。”我回答说。
“文法不对,意思没错。”
他回到工作台,拿回来一样东西,看上去既像是条肥大的布腰带,又像是世上最薄的电热毯。上面悬着一条电线,上面连着一个白色塑料盒子,盒子上面有个滑动开关。雅各布斯手里拿着布腰带,凝重地看着康拉德。“这是我去年一年断断续续在鼓捣的项目。我称之为电神经刺激器。”
“这又是你的发明吧。”我说道。
“不完全是。使用电来限制痛感和刺激神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想法。耶稣基督诞生前60年,一个名叫斯克瑞博尼·拉戈斯(Scribonius Largus)的罗马大夫发现如果病人牢牢地踩在一条电鳗上,腿脚的疼痛可以得到缓解。”
“你瞎编的吧!”克莱尔边说边笑。康拉德没有笑,他充满惊奇地看着那条布腰带。
“绝对没有,”雅各布斯说道,“不过使用小型电池作为电源,这倒是我的发明。在缅因州中部要找电鳗很难,要把它绕到男生的脖子上就更难了。这正是我希望使用刺激器达到的效果。雷诺医生说你的声带并未撕裂,这点他说得可能没错,康拉德,不过需要给你的声带加把力。我愿意做这个实验,不过关键看你。你觉得呢?”
康拉德点点头。在他的眼中我看到了一种消失已久的神情:希望。
“你怎么没在卫理公会青少年团契给我们展示过?”克莱尔问道。她听上去就像在发难。
雅各布斯看上去很吃惊,而且有些许不安。“大概是因为我想不出怎样把它跟基督教课堂结合到一起吧。我一直想着在阿尔·诺尔斯身上测试这个装置,直到杰米今天来找我。知道他的那次不幸事故吧?”
我们都点点头。他在土豆筛选器里丢了几根手指。
“他还能感觉到已经不存在的手指,说感觉手指痛。而且由于神经伤害,他那只手的移动能力也受到了限制。正如我所说,我很多年前就知道电可以在这些地方帮上忙。看来你要成为我的小白鼠了,阿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