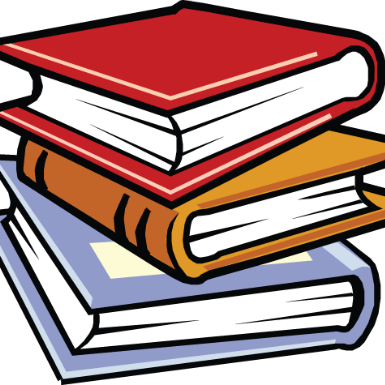张连义终于放下心来,他本能地感觉,此时的妻子已经大致恢复了正常,或许只是因为被阴魂附体的时间太长,所以脑子里还残留了一点别人的意识而已。
他俯下身,慢慢地扶起妻子的身体,嘴里尽量轻柔地说道:“他娘,起来吧!地上凉,看别冻坏了身子。”
女人的眼睛在张连义脸上仔细地审视着,眼圈逐渐红了起来:“他爹,我刚才……我刚才好像做了一个梦。这是咋回事啊?我怎么……我怎么躺在地上了?”
张连义不敢告诉她真相,只是柔声安慰:“没事,可能是你这段时间累着了,刚才我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你躺在地上,可能是晕倒了吧,休息休息就好了。”
女人摇摇头,有点踟蹰地说:“不对,刚才我好像听见有人在说话,而且好像是和强子有关。就是……就是现在我好像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脑子里总像是有一些影子在晃,可是又怎么也看不清楚。你说,强子他……强子他不会真的出啥事吧?”
张连义忽然间有些烦躁,正想发火,但是看着妻子那憔悴柔弱的样子,却又有些不忍。他努力平静着自己的心绪,这才想起了自己赶回家的目的。看看妻子好像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这才小心翼翼地问道:“他娘,我记得昨天晚上我从院子里回屋的时候,好像听见你一直在说一句话,而且还叫着强子的名字。那时候,你到底是想说些什么啊?”
强子娘眼里一片茫然:“我说了吗?我怎么啥都想不起来了呢?”
张连义叹了一口气,心说算了,看来妻子昨晚也就是做了噩梦之后,脑子有些不清醒吧,她说的那些话,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其实,虽说他潜意识里也觉得强子可能出了啥事,却也不愿意去相信这些:强子不比虎子,虽说倔强,但是却一直很守规矩,相比较大多数同龄人来说,应该还算得上是少年老成的那一类人,再说这次‘出伕’带队的栓子叔做事周全老道,有他看着,还能出啥大事不成?
他扶着妻子慢慢站起身,想要扶她去炕上歇息,没想到这时候女人的目光无意间落在了摆在八仙桌上的神龛和木人上,就见她突然间浑身颤抖,嘴唇哆嗦着,指着桌子上的那些东西叫了起来:“是他!是他!是他把强子和虎子带走了!而且,而且强子还怨我不听那人的话,所以那人就把他带到一个很深、很黑、很冷的地方去了!”
张连义一怔,脸上的神情逐渐冷了起来:“是吗?他还说什么了?”
女人身体一僵,慢慢地向他转过脸来,神色间已经充满了阴狠的意味,她慢慢地把嘴凑到他的耳边,一字一句地拉长了声音说:“他还说,要是我们再不听话,那人就会把我、你、还有莲花,全都带到那个地方去呢!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张连义并不退缩,直视着妻子的眼睛,用非常认真的口吻说道:“是吗?!你说的这些,我确实挺害怕的。不过,你得弄清楚一点:这件事不是我在求你,而是你在求我!你想用这种手段来要挟我,不觉得有点可笑吗?你也别跟我提什么契约,那些东西是你一千多年前跟那个长弓签的,跟我无关!或许你觉得长弓替你做事顺理成章,因为他是你们的家仆,但可惜现在是新社会了,你们那时候的那一套,现在早就行不通了,那个什么劳什子契约,对现在的张家人来说,也根本没什么效力。你想让我帮你,那好,拿等价的东西来换!”
强子娘嘴角下弯,脸上露出了一丝嘲讽的笑意:“他爹,那你想要什么啊?”神态间竟是充满了娇媚。
张连义心中一荡,一瞬间竟是有些神不守舍,他连忙把目光避开对方的脸,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别的,把以前我失去的,全都还给我!虎子、房子、财产、田地!”
强子娘‘咯咯咯’地笑了起来:“他爹,你好贪心啊!不过,你觉得你有资格跟我讲条件吗?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给你个梦想成真!”
说完挣开张连义的手,一步步走到门口,猛地打开了房门。
院子里脚步声响,村长和栓子叔满脸沉重地走了进来。
……
按照农村的规矩,在外凶死的人是不能再运回家里停放的,和虎子一样,强子的尸身只能当天火化,然后把骨灰直接下葬,而且,他们还都不能葬入祖坟。
看着野地里那两个并肩而立的坟头,再看看身边满面笑容,显然已经有些神智失常的妻子和抱着她的大腿‘嘤嘤’哭泣手足无措的莲花,张连义心里一片冰凉。他不知道,随着两个儿子的先后去世,自己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难道,这就是当初那个皮子山还有后来的五爷爷曾经许诺过他的,那些‘仙主’可以赋予他的巨大好处?!
身边帮忙的乡亲们已经逐渐散去,早春的傍晚,风卷起去年冬日遗留的落叶堆积成满地斑驳的凄凉,田野间暮霭渐起,风声如泣如诉。张连义忽然笑了起来,那笑声伴着三个踟蹰的背影愈去愈远,天地间似乎充满了阴森森的鬼意。
晚饭,只有强子娘一个人若无其事地吃着,对于白天发生的事情,她似乎无所萦怀一般。只不过偶尔的,张连义也能从她眼里看出一点忧伤闪过,却总是一闪即逝。
房间里还是三个人,但是浓浓的哀伤却已经挥之不去,就连莲花那张天真的小脸上也早已看不见笑容。感受着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冰冷和娘脸上的毫不在乎,这个小姑娘似乎也能察觉到这个夜晚的不同寻常。她没有依偎在娘怀里撒娇,因为她看向娘的眼神里竟有着莫名的畏惧;她也没有去纠缠爹,去为自己幼小无助的心灵寻求那种本应是理所当然的抚慰,因为爹身上的那种冰冷让她从心底里不寒而栗,不自觉地只想远离。
小姑娘一个人默默地洗脚,脱衣上炕钻进被窝,细细的呼吸中不时夹杂着一声声哽咽。这个小小的人儿,过早的,领会到了这个世界的残酷。
张连义搬个马扎,一个人面对着八仙桌静静地坐着,不做声,只是一直接一支地抽烟。朦胧的烟雾缭绕着,短短的一天时间,他的脸色已经变得消瘦而又苍白,一双原本还算得上有神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往事如潮水般在他心里循环往复,一幕接着一幕。
炕上,强子娘依旧如往日一般就着昏黄的煤油灯光做着一双千层底的黑条绒布鞋,麻线在鞋底和鞋帮之间穿过,‘嗤嗤’作响。张连义无意中斜眼看时,竟突然间怒火勃发:那双鞋,是给强子做的!
这样的情形之下,一个男人、一个中年丧子的男人、一个两年之内连丧两子的父亲、一个原本时时刻刻做着失而复得之梦的往日少爷、一个面对着妻子从温良贤淑乍然变得冷酷无情已如陌生人的丈夫,又如何让他继续保持冷静和理智、儒雅和风度?
张连义猛地站起身来,一声不吭地抢上前一把将妻子手里的布鞋抢过来,顺手拉开房门扔了出去。他瞪着红红的眼睛紧紧地逼视着妻子,那神情,完全是在面对着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一般,用一种吃人一样的语气,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你他妈的到底是谁?!强子已经被你害死了!害死了!你这样虚情假意,装给谁看?!”
强子娘先是一愣,眼圈微红,然而脸上的表情却是如冰山一般的阴冷:“他爹,你这是咋了?胡说什么啊?强子他现在好好地跟我在一块呢!天冷了,我给他做双鞋子穿,你干嘛扔掉啊?”
说完不再理他,自顾自下炕走出房门,把鞋子拾了回来,旁若无人地爬上炕,很认真地继续做她的针线活。
此时的张连义几近崩溃,他发了疯一样一下子扑到八仙桌前,一把抓起神龛高举过顶,拼命地摔在地上,像个疯子一般咬着牙,一脚接着一脚地拼命踩踏。
神龛碎了,那张血红的‘仙’字也被碾成了一地碎屑。
房间里越发阴冷起来,一如强子娘瞟向丈夫的眼神。
第089章 开仙门
河边的杨柳已经抽出了点点嫩芽,田野间,平展展的麦田里也有了生命的萌动,天是渐渐地开始回暖了,河水也已经开始不知疲倦地汩汩流淌。张家庄的‘出伕’队伍早就回家,乡亲们又开始了按部就班的一年农忙。对于他们来说,不管是虎子也好,强子也罢,黄泉路上无老少,既然已经走上了那条不归路,那就已经是古人了。或许会有一些茶余饭后的感叹,也或许会有一些偶尔为之的唏嘘,但这些毕竟已经过去了。事不关己的时候,人们总是善于遗忘的。
然而,张连义家那座刚刚落成不过几年的农家小院,却再也回不到从前。与渐趋温暖热闹渐趋生机盎然的天气相反,小院里越来越是冷寂,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阴沉沉的,一天到晚充满了死寂。
从那天开始,强子娘仿佛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每天沉浸在一个只属于她自己的世界里,强子和虎子的衣服鞋袜一件件地做了出来,整整齐齐地叠放在炕头上。每天一早一晚,她总是会准时地去两个孩子的房间里打扫收拾,早上叠被,晚上铺炕,甚至是一日三餐的饭桌上,她也依旧是认认真真地摆放好五副碗筷,生活仿佛一如既往,根本看不出一丝一毫的变化。对于丈夫的指责和冷言冷语,她总是一笑了之,不争吵,不辩解,使得张连义每次一进家门,就好像进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潭,平静,却又沉闷得让他喘不过气来。
刚开始,张连义还只是在实在是压抑得受不了的时候,才会偶尔在村委那间会计室里对付一宿,算是暂时避开一下家里那种看似平静实则诡异的氛围,给自己压抑的心情做一下放松,只不过为了掩人耳目,也因为会计室里并没有床,就这么趴在桌子上睡觉实在是不太舒服,所以他还能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按时回家吃饭、睡觉。然而随着天气迅速转暖,再加上家里那种诡异的气氛越来越是浓重,到了最后,他干脆从家里把被褥带到村委,偷偷锁在一个闲置的柜子里。到了晚上,他回到家匆匆忙忙地吃几口饭,然后回头就走,就把那张白天办公用的桌子当成了床铺,一个人倒也清静,心里竟是说不出来的轻松。
而且更让他高兴的一点是:只要他睡在村委,以前那些乱七八糟的梦就不会再出现,而且他还不用整天睹物思人,虎子和强子在他心里造成的创伤也好像正在渐渐平复。
对于他的夜不归宿,他不解释,强子娘居然也从不过问,就好像在她眼里,这时候的张连义妇女反而成了两个透明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人。这也使得张连义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生出了些许失落和伤心:那些曾经你贪我爱好得蜜里调油的好日子,就这么一夜之间完全改变了模样,失去了、不见了、再也找不回来了。
极度的失望之下,张连义也不再忌讳什么,他从集市上买来一套简易的锅碗瓢盆,借着村委日常烧水用的煤泥炉烧火做饭,就这么正大光明地住在了村委。刚开始的时候,村委那帮同事还都问过他,也劝过他,但是他却只是笑笑不说话,不反驳,也不解释,只是该咋不回家还是咋不回家。
这样时间长了,大家也逐渐习惯了他的这种生活状态。除了偶尔会有人感叹一下什么白发人送黑发人、中年丧子等等人生的无奈和悲哀之外,向他投来一抹同情而悲悯的目光之外,也不再有人多说什么。
时间过得很快,眨眼间春天已经过去,一场淋漓尽致的透雨过后,夏天突如其来。
张家庄距离乌河还挺远的,夏季村庄里的排水,主要依靠的就是村里村外的几个大湾,也就是或天然或人工刨出来的一种储水的水塘。这些湾子之间互不关联,自然也不能流动,所以这水流进去之后,便成了一潭真正的死水,到了夏季,这些湾子也就成为了蚊虫滋生的圣地,加上村庄周围有许多零星分布的草甸子,也非常适合蚊虫藏身,所以夏天的张家庄,真正是蚊虫肆虐,往往天刚一擦黑,大片大片的蚊子就成群结队地飞了出来,吹着喇叭在村庄里四处扫荡,不分人畜鸡鸭鹅狗猫,遇见活物就一哄而上,端的是让人防不胜防、烦不胜烦。于是每到这种时候,蚊帐就成了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
在村委熬了几宿之后,张连义就有点扛不住了。这村委会计室虽然清静,但一个人身上的血那可是有数的,总不能全喂了蚊子吧?无可奈何之下,张连义收拾收拾,终于回家了。
一进门,院子里似乎依旧是收拾得井井有条,灶房里的烟气还没有完全散去,堂屋里亮着灯,饭菜的香气从竹帘中透了出来。张连义心里一暖,家的温馨已经久违了,一刹那间,他甚至觉得眼睛有些酸酸的,脑子里想象着老婆和女儿笑吟吟的脸庞,还有那张小小的饭桌、可口的饭菜、不凉也不热的稀粥。仿佛直到此时他才终于意识到,原来自己好像已经很久没回家了。
老婆这段时间恢复得怎么样了?莲花没生病吧?学习还跟得上趟吧?家里的蚊帐……挂上了吧?还好,门口的竹帘已经挂好了,这个,以前女人是不会沾手的,这都是自己的活。
他甚至是有些急切地向屋门口走去。
隔着门帘,灯光投映着一个落寞的背影,隐隐能看到一头长发披肩,与一袭白色的长袍形成了鲜明的色差对比。张连义忽然觉得心里一跳,这种款式的衣服,根本不是时下流行的样式,不但家里从没有过,而且很明显的,就算是张连义已经活到了近五十岁,还从未在现实生活中见过——那种衣服,只在戏台上看到过。
张连义伸出去的手迟疑了,那个背影很熟悉却又有些陌生,那是自己的妻子吗?他心里有些恍惚起来。迟疑了好一会,他才试探着叫了一声:“他娘,是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