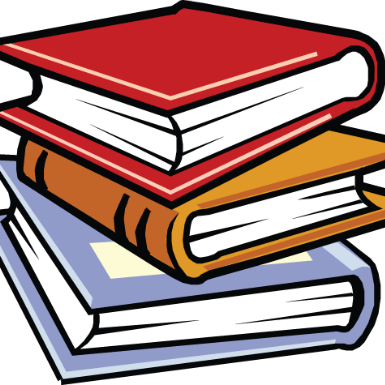“从此五通神在绍德城没落了,不过不走正道、捞偏门的,偷偷拜五通的多少还有些人。你想,做小偷的,做强盗的,窑子里的,甚至拐小孩的虎姑婆,拜正神也没用啊。你总不能对关老爷说,‘二爷吉祥,明天您保佑我开市大吉,多偷多抢点儿。’或者对观音菩萨说,‘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好菩萨,求你保佑我多给外面孩子换换爹娘。’只怕没说完就给雷劈了不是?只有这五通邪神,算是大家同病相怜,但万万也没人敢搞血祭。”
“不光祭不起,也没人敢留五通神常住。五通神小气,耳朵也尖,万一哪天生意不好,捞偏门的粗人多,一不小心丧气下把五通神给顺带骂了,被听见就玩儿完了。”
“都是刀尖上打滚的交易,拜神也只是求个心安,谁没事背座山肩上扛着?了不起削个五通神的小木像,逢年过节吃剩的鸡毛鸡血在木像上涂涂,意思你保佑我发财就有肉吃,没生意骨头都没得啃……你娃这是干吗呢,不听赵叔说话转来转去的?”
赵长洪停下不解地看着刘涛。刘涛脸红得真跟涂了鸡血似的:“赵叔,赵叔,我真憋……憋不住了。都怪您又提什么发洪水,再不尿我可要湿裤子了。”赵长洪看看散发着臭气的大洞:“那趁着白大仙没回来,你抓紧解决了。作死啊!那个洞里不能尿!”赵长洪一把拉住跑出圈子对准大洞掏裤洞的刘涛:“那边,那边地上有个小水瘪(土语,很小很小的水坑),对,顶上漏雨的那块。反正这里已经臊翻天了,也不少你娃这一点儿。咦?!”
刘涛站着正要小解,回头见赵长洪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脸更红了:“赵叔您这么盯着,我尿不出来的!”赵长洪连连摆手直凑了过来:“别打岔,你换一边尿去。这事有点儿蹊跷。”刘涛顾不上许多,跑到旁边方便完浑身舒畅,回头一看,赵长洪已经趴在了地上,眼睛都快凑到了水瘪里去,目不转睛地看着什么,好奇地凑过去一看,除了一点儿积着的雨水什么也没看到,不禁问道:“赵叔您看什么呢?”
【八、鼠多咬死象】
赵长洪抬起头来:“你娃年轻眼神好,来看看赵叔是不是老眼昏花看不准。”刘涛也学着赵长洪趴下,只听赵长洪问道:“看到这是什么?”刘涛抓抓头:“坑啊。”赵长洪不耐烦地问:“我问坑里的。”刘涛迟疑道:“水啊……”赵长洪啐了一口:“我说这水面上的!”刘涛犹豫着回答:“霉谷皮,在水波纹圈里转呢。”
赵长洪一拍大腿:“对啊,水里有波纹呢!可是你看这粮仓里有风吗?”刘涛摇摇头。赵长洪压低声音道,“就是!这水瘪可不是大江大河,哪能无风三尺浪?没风这水里的波纹哪儿来的?!”
刘涛摇摇头不明白,赵长洪的脸上渐渐露出了狞笑:“常年打雁,今天倒差点儿给小雀子鹐了眼睛!”刘涛正要追问,忽见赵长洪连连摆手示意他别说话,回头一看那只白鼠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从洞里钻了上来,瞪着滴溜溜的眼珠看着二人。赵长洪慌忙拉着刘涛又回到了圈子里,连连赔笑:“人有三急,白大仙有怪莫怪。”白鼠似乎不想理会赵长洪,看了两人一会儿,转过头去对着洞口。赵长洪朝刘涛使了个眼色,嘴皮动着似乎在说话却没出声。
刘涛好奇地把耳朵凑了过来,这才听见赵长洪用最小最小的声音嘀咕道:“脱棉袄,兜住它!”刘涛不禁一惊正要再问,却被赵长洪凶狠的目光瞪住,眼看赵长洪慢慢解开军衣扣子,眼睛眯起来盯着背对自己的白鼠,显然是不怀好意,和刚才提起五通神时恭恭敬敬的态度天差地别。刘涛迷糊中知道这绍德城的邪门事确实太多,赵大叔说变就变的脸也不是自己能看懂的,有样学样地也脱下了半个袖子,眼见赵长洪已经轻手轻脚地解下军棉袄正要扑过去,刚要配合一下,忽然两人的动作停在半空中,呆住了。
瞬间从白鼠正对的大洞中涌出了一片黑色,细看居然是无数的黑色老鼠组成。每只身形都比白鼠小好多,保持着每四只抬一只的队形,再看中间被抬着的那只老鼠腹部还抱着偌大一只团好的土球。刘涛忍不住惊叫起来:“赵叔,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惊动白鼠回头看来,正好看到赵长洪兜着衣服踮起脚尖保持着撒网姿势,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讪讪地抖了抖衣服,边穿回衣服边打着哈哈:“这么多土啊,难怪衣服上尽是灰,掸掸,掸掸……”
但说什么也没用了。只见周围无数的黑鼠在腐草间放下土球,白鼠带头一步步朝赵刘二人逼了过来。顿时四面八方厚实实黑压压的一团,刘涛腿都软了,逃都不敢逃,生怕一脚跨出去踩着滑兮兮的鼠肉,跌倒立刻就被群鼠啮了。赵长洪慌忙摘下墙上的油灯,倒出灯油在两人周围点燃了一个不大的火圈,哭丧着脸道:“这下全完了,也不知道是该骂你娃呢还是该谢你娃。刚才要是你不张嘴你赵叔动作快点儿,没准儿能把那带头的白耗子给捞住谈谈条件。可要是一失手……现在估计连骨头都剩不下了。”
刘涛奇道:“谈条件?和谁谈条件?”
赵长洪长叹道:“你娃想啊,粮仓不透风水坑面上怎会起波纹?那是因为这里有声音才把水纹震荡起来了。你赵叔走南闯北看过西洋马戏团,能用一种特别的暗哨来指挥养熟的动物做事,让狗啊耗子啊叼纸牌什么的,但看马戏的人却发现不了。因为耗子或者狗的听觉比人灵,能听到人听不到的哨声。那只被我当成五通神里白大仙的白耗子,准是有人长期训练养着的。马六马七,准落到这人手里去了。”
“你看这白耗子用起来就跟自己的眼睛手脚一样方便,那人一定金贵着呢。能逮住耗子他就得听咱们的。可谁想得洞下还伏着这么多黑耗子?这回咱爷俩真要死得骨头也剩不下啦!”
说话间群鼠已经将火圈团团围住,一双双鼠眼倒映着火光,依稀可见口中凸起的雪亮鼠牙。
【九、吹起打狗哨】
刘涛急道:“赵叔您刚才说有的声音老鼠能听见但人听不见?”赵长洪没好气地道:“这会儿你还不信?”刘涛连忙摇头道:“不是不是,我就是记得您还说这种声音狗也能听到?”赵长洪“嗯”了一声,忽然眼睛一亮。
果然刘涛忐忑地说道:“小时候我看我家狗场的狗,有的时候会竖起耳朵一动不动老半天,眼睛直愣愣地像在听什么,但人在旁边一点儿听不到动静。后来问我爹,我爹说那是很远很远的地方有猎人在打狗哨呢。这算不算是你说的那种声音?”赵长洪沉吟道:“打狗哨?”刘涛鼓足一口气,把食、中二指塞进嘴里用力地吹了一下,但是一点儿声音也没发出:“就这样。山里的猎人发现野猪兔子什么的要通知猎狗,但又怕惊动了猎物,就打这种没声音的哨子……”
赵长洪忙着一脚把一只钻进火圈着了火的黑鼠踹飞了出去,急道:“不管有用没用,死马都得当活马医,你再打几声试试!”刘涛点点头,鼓起腮帮子玩儿命又吹了一下,结果不吹哨子还好,一吹轰地一下群鼠疯了一般奔着冲进了火圈,直往两人身上爬。好在天寒两人的裤管都扎在厚厚的绑腿里,不然立刻就会钻了进去。刘涛尖叫起来拼命地跺脚再也顾不上打狗哨,赵长洪边甩着腿上的老鼠边吼叫:“有用!有用!继续吹,继续吹哨子!”刘涛急得哭了出来:“没用啊!赵叔你吓糊涂了吧,您看这耗子疯的……”
赵长洪左边裤管被一只老鼠咬了个洞钻了进去,忍不住也尖叫了起来,边玩儿命地拍打边吼道:“没用耗子能忽然变得这么疯吗?你没看那只领头的白耗子在那儿慌得直转圈子不知道怎么好吗?你娃是不是吹错了调子?这群耗子怎么忽然跟喝了小公鸡血似的得劲?”刘涛啊了一声:“赵叔您说的没错,我吹的是猎人发现猎物让猎犬进攻的狗哨!要不,要不我吹个打完猎让猎狗回头收猎的哨子试试?”
赵长洪手忙脚乱中跌倒在地,立刻被耗子没头没脸地铺满了,拍打中除了嗯嗯之外连嘴都不敢张,好在等刘涛再次吹起狗哨,群鼠的动作渐渐停住,看向领头的白鼠犹豫不决。赵长洪一口咬断了一只不知趣还往自己领子里钻的黑耗子的尾巴,耗子惨叫着逃窜了出去,赵长洪趁机喘着粗气爬了起来,吐出耗子尾巴:“看不出你娃还有这个能耐,好样的。”
刘涛露出得意的笑容:“打狗哨我七岁就偷偷学会了!赵叔你别忘了,我家祖传养狗的,在东北老刘家狗场的狗……”赵长洪苦笑道:“祖宗,夸你两句就上天了。咱爷俩只怕眼下就要去见你老刘家的狗了。你回头看看后面那火!”
刘涛扭头才发现,原来刚才因为群鼠扑过火圈,有些身上沾了灯油被烧得乱窜,或是被赵刘两人乱踢乱甩,迅速燎着了地上的稻草,尤其是门口的草堆,已经成了一团巨大的火球,将门烧得严严实实,就是铁打的金刚想钻过去只怕也要化成铁汁,更不用说沿着地上的稻草窜过来的火势了。若不是早前群鼠散在地上的从洞里挖出的无数土球堵了一堵,只怕整个粮仓已经成了铁匠铺的烘炉。
但全烧着反正也是眼皮底下的事。群鼠停下啮咬只怕三成是被自己的狗哨吹晕了头,七成倒是怕了这转瞬即至的火。刘涛看看自己和赵长洪身上被咬的千疮百孔,到处露出棉絮的棉军衣,感觉就像两根引火的油灯芯子,实在没勇气走进火里钻逃,正慌乱间被赵长洪一把扯住袖子,喝道:“跳!快往洞里跳!”眼见白鼠带着一群耗子正狼狈地钻入地上的大洞逃命,哪还顾得上细想,连步枪也顾不上拿,两人就一起跳进了巨大的土洞。
【十、死人财,聚宝洞】
洞挖得颇深,好在底下有先逃进来的群鼠垫底,赵刘二人高高地掉下来,跌在无数的鼠肉团上,压得群鼠叽叽乱叫纷纷逃避,一阵心血翻腾倒没受硬伤。刚刚爬起立足,刘涛忽然听到赵长洪低声说:“马家兄弟死了,我旁边应该就是他们的尸体。”
刘涛惊道:“什么?”赵长洪不答,只听群鼠叽叽的叫声中夹着一阵窸窸窣窣的摸索声,不久赵长洪又道:“错不了,帽子上是军徽,肩膀上有番号,身上还有油烟味。身材瘦瘦脸上没肉八九是马七。嗯嗯,旁边这个一定是马六,奇怪,怎么这死胖子脸上也没肉,还滑滑的……等下,他身上有打火机!”
忽然黑漆漆的洞里亮起了一团微光。刘涛欢呼一声,随即变为惊叫。原来地上正是马家兄弟的尸体,不远处还有几块参差不齐的木板。只见尸体破破烂烂血肉模糊,有的地方已经露出了森森白骨。赵长洪边将满手的血在棉衣上擦拭边喃喃地道:“难怪脸上没肉,原来都被啃光了。娃娃你给我拿着打火机,我看看还能搜出什么。”
刘涛胆战心惊地接过血淋淋的打火机,一晃间看到不远处的洞壁上鼠群正堆堆叠叠地窝成一只巨大的鼠团,无数的鼠眼瞪着自己,却像怕了自己手里的火光不敢扑过来,寒毛直竖再也不敢看第二眼,只敢看地上马六马七残缺的尸体,想着不久前两人还是和自己说话吵笑的战友,一阵心酸,险些掉下泪来。眼看赵长洪仔仔细细地摆弄着地上的尸体,连棉衣旮旯都撕开查看,忍不住道:“赵叔,您就别这么损了。人都死了,您还这么翻来翻去拿人家东西。都是穷当兵的,您还能找出宝来不成?”
赵长洪冷哼道:“你娃懂毛,死人永远比活人金贵知道不?人死如灯灭,啥东西留着也是浪费,你赵叔就有这么一个勤俭的习惯……这马六当厨子可真是往死里捞,说南方人不吃辣还藏着这包干辣椒,没收没收!”忽然欢呼一声,“找到了。你赵叔猜得一准儿没错,这找到的不是宝是什么?”
刘涛睁大眼睛呆住了。赵长洪摊开的手心里,赫然是几颗金豆子,在火光下闪闪发光。只见赵长洪咧开剩不了几颗牙的嘴,笑得山羊胡子一抖一抖的,将金豆晃来晃去,嘴里不停念叨:“你娃可别打主意啊,这可是你赵叔一个人掏出来的!难怪马六马七要跑,有这宝贝疙瘩,谁愿意待在绍德城里等死啊。我再搜搜,没准儿嘴里还含着啥宝贝。”
看着赵长洪盯着死去战友的嘴巴跃跃欲试,刘涛实在看不下去,劝道:“叔,您就少做点儿孽吧。我才不跟你抢,就是掏出再多金子来,咱俩也找不到活着出去的路啊。到时候你愿意有人来这么扒弄你身子,拿你东西啊?”
赵长洪呸呸了几口:“童言无忌,童言无忌!你娃少给我说点儿这不吉利的。谁说东西是他们的了?马六马七要是早有这宝贝,在城外那会儿就溜了,还等现在绍德被围得铁桶似的才找地方躲?一准儿在这附近摸的!”
“告诉你娃,你赵叔在绍德城里活了几十年,早听说林家有个世代敛财的聚宝洞,没想到这回被马家兄弟发现了踪迹,可惜却没命享受。你娃不是奇怪为啥会有木板盖在洞口吗?那是这两兄弟想吃独食,发现了宝贝,怕咱爷俩进来吃饭时发现不对劲要找来分钱,才在跳洞前拖来木板盖了个严实,准备躲里面等我们都战死了,趁进城的日本人不注意再开溜。可打的一手如意算盘最后却便宜了你赵叔。本来嘛,这绍德城地邪,绍德的财,只有绍德人能发,没这个命谁能发这个财?!”
赵长洪只管絮叨,忽然洞里响起了一个阴阳怪气、吐字不清的声音:“老头子你的说滴不对,中国人滴地方,都是大日本东亚共荣圈滴干活。大东亚共荣圈滴财,就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滴财,就不可以给你们中国人发滴!”
刘涛吓得愕然大叫:“有鬼!有鬼!还是一日本鬼!”慌忙举起打火机四照,却怎么也看不到洞里有第三个人的身影。
第五章 星君棋谱
【一、收尸人】
此时伏龙塔上陈参谋正说道:“那夜席间,我因为交谈中听到绍德市长早年曾跟随中山先生,在日本与黑龙会有过交往,便随口问市长以往可曾听说在日本本土有没有什么组织,习惯蒙面穿黑衣,胳膊上还有犬形文身的。市长说从没有听闻过,旁边一名年高的幕僚正好酒多了,笑着插嘴道:‘犬形文身没见过,穿黑衣蒙面的绍德倒是天天见,城里那么多收尸人不都这副打扮吗?’”
“这句话让我打了个激灵: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瑶光死后第三天离开南京的日本特使团,难道和电文所指消失在绍德城里的寿老人是同一伙人?那绍德城不就是特使团的最后落脚点?这场鼠疫的形成,难道是丧心病狂的日寇为了掩护特使团进城而不暴露身份所制造的烟幕弹?老幕僚接下来的话更验证了我的想法,他愤愤地絮叨道:‘说起这些收尸人,真是人心不古,贪婪败德!早前收尸的人手原本够用,不料用着用着人头就少了,想是因为趁火打劫从死人身上搜刮财物,眼看捞够了就跑路了。’”
“这种丧尽天良的做法,跟掘墓挖坟又有何区别?记得几十年前在绍德城就发生过多起发死人财的盗墓案,导致民愤鼎沸,一致要求将盗墓贼砍头示众,结果还是让犯人逃了。所以这次我一发现这种情况,没来得及汇报市长便让卫兵在城门设下关卡,规定出城必须检查搜身。”
“封城搜身一举真是天助我也,那日本特使团因此被卡在城里出不去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只听老幕僚还在摇头晃脑地表功:‘当年讨伐盗墓妖人的罪檄正是我亲笔所写,曾在绍德城轰动一时,传诵经年,檄文里说,兹有妖人……’我慌忙打断他的炫耀:‘老先生所说甚是有理,收尸人此举实在可恶!’”
“既然染病的尸体烧得差不多了。若不怕被非议为过河拆桥的话,还请市长先生立即下令逮捕所有收尸人,如搜查出趁机打捞死人财物的,必须严惩以儆效尤。否则只怕他们捞顺手了,捞完死人就抢活人也难说得很。暗想事急从权,虽然我这么说对绍德城里的收尸人有失公允,但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老幕僚一听我赞扬他的主意,大喜:‘真是英雄所见略同,陈长官的建议实在刻不容缓。市长你想,抢劫活人还算好的,万一今夜外面的收尸人眼见尸体烧得差不多后面没财路走,想着最后捞一笔,拿闷棍打死活人搜口袋怎么办?你说这人一被打死往火堆里一扔,回头谁知道是得鼠疫死的,还是闷棍打死的?他们捞完钱就跑路,留下的罪名大家难免算在……’市长听得张口结舌酒醒了一半,连忙安排宪兵配合我们突击逮捕了所有的收尸人。细审之下还真揪出了几个害群之马,不过更有价值的情报是,正如那位幕僚先生在席间所说,在扑灭鼠疫的过程中,确实有十几个收尸人不见了。”
“据有的收尸人回忆,这次确实见过同行里面有人在搬运尸体的时候不经意露出过胳膊上的犬形文身。然而我们搜身后发现,捕回来的收尸人胳膊上却全部干干净净。再细审之下得知,很多在不同地方的收尸人都回忆起有同伴在很短的时间内走开一下,却再也没有出现在绍德城里。起先众人还抱怨那些人是不是偷懒想逃避重活,再仔细想想,所有收尸人都惊恐地回忆起,原来早先和自己一起搭尸体的蒙面同伴里,总有个别是从头到尾也没说过话的。而走开后消失的正是那些沉默寡言的收尸人。”
“一两个收尸人这样说还不足为奇,但大量出现这种诡异的现象就完全证明了我的猜想。那些消失的收尸人正是在南京出现过的黑衣日本使团。毕竟日本人和中国人在举止相貌上还是有差异的,而且听南京的洗衣工说,那些日本人也不是能很娴熟地掌握汉语,十几个这样的日本人陡然进入绍德城里,必定难以掩饰。所以为了掩盖这些无法弥补的特点,才有了这场鼠疫,帮助他们化妆为理所当然必须蒙面遮住尸臭的黑衣收尸人,更让绍德居民无法随意行走盘问。”
“而这一切,从使团到达南京,除了统一合身的黑衣就没换过别的衣服看,这根本就是一场在日本本土就策划好了的阴谋,目标直接指向的就是绍德城。可是照席间那位老幕僚先生所言,那么多日本特工是不可能就这样丝毫不惊动关卡走出绍德城门的。那为什么现在他们都不见了,就像绍德城里有什么巨大的隐形怪物把他们都吞噬了一样。”
【二、阴阳术】
俞万程听了陈参谋的话,笑道:“你这可说得太玄了,一口一个神魔怪物的,倒让我想起在日本留学时听到的那些关于阴阳师的传闻。”陈参谋眼眸中精光闪动:“哦?师座也相信阴阳星相一类的学问?听说日本最著名的阴阳师是平安时代中期的安倍晴明,被誉为藏传佛教密宗与道教拘神符咒之集大成者,一度被日本皇室持重,不知道可有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