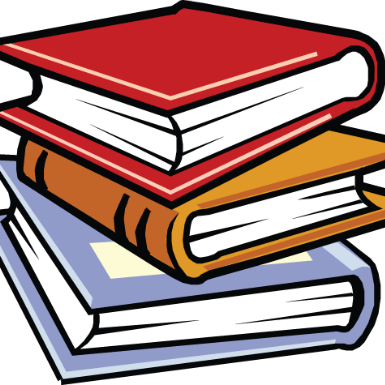I 第五先生/骷髅山/太平湖
我们的生活至少有一个方面像极了电影。主演阵容由家人和朋友构成。配角由邻居、同事、老师和日常见面的熟人来充当。还有其他客串演员:超市里笑容甜美的收银员,当地酒馆里友善的酒保,还有你在健身房里一周三天一起健身的伙伴。然后就是成千上万的临时演员——那些人就像水流过筛子一样从我们的生命里经过,只打过一次照面,然后再不相见。在巴诺书店里看漫画小说的少年,你必须侧身挤着过去(小声说句“借过一下”)才能到杂志专区;旁边车道上,那个趁着红灯停车赶紧补一下唇彩的女人;你在路边餐厅吃个快餐,旁边那个为小宝宝擦掉脸上雪糕的母亲;棒球赛上卖了包花生米给你的小贩。
但有时候,有这么个人,他归不进上面任何类别,却走进了你的生命。这就是打牌时偶尔抽到的大小王,往往在危急关头才出现。在电影里,这类角色被称为“第五先生”或“促变者”。他在电影里出场的时候,你知道他绝对是编剧有意安排的。但谁是我们生活的编剧?是命运还是巧合?我多么情愿相信是后者。我发自内心出自灵魂都希望是这样。当我想到查尔斯·雅各布斯——我的“第五先生”、我的“促变者”、我命中的劫,我不愿相信他在我生命中的出现跟命运有任何关系。因为这就表示所有这一切——这些恐怖事件——都是命中注定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根本不存在光明,我们对光明的信仰只是一种愚蠢的妄念。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就是活在黑暗之中,像活在地穴里的动物,或是藏在小丘之中的蚂蚁。
而且我们身边还有别的存在。
在我六岁生日时,克莱尔送了我一套玩具士兵。1962年10月的一个星期天,我正排兵布阵谋划一场重大战役。
我来自一个大家庭——四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总能收到很多礼物。克莱尔送的礼物一直是最棒的。或许因为她是老大,或许因为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儿,或者两方面原因都有。不过那些年里所有她送我的宝贝礼物中,那支军队是最棒的,完胜其他礼物。有200个绿色塑料士兵,有的持步枪,有的持机枪,有12个士兵焊到了像管子一样的东西上(她说那些是迫击炮)。还有8辆卡车和12辆吉普。这套士兵最酷的地方就是那个包装盒了,那是一个用硬纸壳做的军用小型手提箱,涂着黄绿色迷彩漆,正面印着“美国军方财产”字样。下面是克莱尔自己印的:杰米·莫顿,指挥官。
就是我啦。
“我在特里的一本漫画书背面看到的广告,”等我欢喜地一阵狂叫过后,她说道,“他不让我把广告剪下来,因为他就是坨鼻屎——”
“没错。”特里说道,他那时八岁。“我就是鼻屎哥。”他伸出手,将食指和中指分开,捅进自己的鼻孔。
“住手,”妈妈说道,“过生日的时候不许兄弟之间起争执,劳驾,谢谢。特里,把手指拿出来。”
“反正,”克莱尔说道,“我把优惠券复印之后寄了回去。我还担心不能及时寄到,结果真到了。你喜欢我就满意了。”她亲吻了我的太阳穴。她老喜欢亲那里。这么多年过去,我还能感觉到那温柔的亲吻。
“超爱的!”我把军用手提箱抱在怀里说道,“我会永远爱它!”
当时是早餐过后,那天的早餐是蓝莓薄饼和培根,我的最爱。我们几个过生日的时候都能吃到自己最爱吃的东西,礼物都是早餐之后送,就在厨房里,一个壁炉,一张长桌子,还有那笨重的洗衣机,坏了又坏。
“杰米说的‘永远’就是……5天的样子。”阿康(康拉德的昵称)说道。他当时10岁,身材修长(后来发福了),那时候就热衷于理科了。
“说得妙,康拉德。”老爸说。他穿着干净的工作服,他的名字——理查德——用金线绣在左胸的口袋上,右胸写着莫顿燃油。“很了不起。”
“谢谢,老爸。”
“鉴于你这么能说会道,帮妈妈清理早餐碗碟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明明轮到安迪了!”
“现在不是了。”老爸边说边给最后一块薄饼浇上糖浆,“拿块抹布去,口才大师。别打碎东西。”
“你把他都宠坏了。”阿康回嘴说,不过还是拿了块抹布。
康拉德对我“永远”的说法倒也不完全错。五天之后,安迪送我的“小小手术台”游戏就在床底下积灰了(反正身体器官本来就不齐,安迪是在尤里卡田庄杂物甩卖上花15美分买回来的)。特里给我买的拼图也是。阿康送了我一套插胶片看的立体眼镜,持续的时间稍微长了些,但最终还是进了我的储物柜,从此无影无踪。
爸爸妈妈送了我衣服,因为我的生日在8月末尾,而那一年我该上一年级了。我觉得新衣服新裤子就跟电视信号测试图一样无趣,但我还是尽量满怀热情地谢了他们。我料想他们肯定一下子就看穿了,对于一个六岁小孩儿来说,热情不是这么好装的……不过说来可悲,这项技能我们大多数人都学得太快。不管怎样,衣服就在洗衣机里洗了几回,挂在院子侧面的晾衣绳上,最后折好放进我的衣柜里了。不用说,这些衣服眼不见心不烦,一直搁到9月份才拿出来穿。我记得有件毛衣挺酷的——棕色带黄条。穿上去的时候我假装自己是个名叫人肉大黄蜂的超级英雄:坏蛋们,当心我的刺!
不过关于那个装着士兵的军用手提箱,阿康倒是说错了。我一天到晚都在玩那些士兵,通常在前院的边上,在我们家的草坪和卫理公会路之间的那条狭长的泥沙带上。卫理公会路那时候其实也就是一条泥土路。除了9号公路和通往山羊山(那里有个富人的度假村)的双车道之外,哈洛镇上那时候所有的路都是泥土路。我记得有好几次妈妈因为夏天干燥尘土吹进家门而苦恼。
我和比利·帕克特和阿尔·诺尔斯——两个我最要好的朋友——一起玩塑料士兵度过了许多个下午,但是查尔斯·雅各布斯第一次出现在我生命中的那天,我是自己一个人。不记得为什么比利和阿尔没跟我在一起,不过我确实记得当时自己一个人玩还挺开心的。其一,这样就无须把士兵分成三队了;其二——这一点尤为重要——我不用再跟他们争这次该谁打胜仗了。其实,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打败仗的道理,因为这可是我的士兵,还有我的军用手提箱。
就在我生日刚过不久的一个夏末,我跟妈妈透露了这个想法,她握着我的肩膀,看着我的双眼,我立刻就知道她要给我讲人生大道理了。“杰米,这世上半数问题都来自这种‘这是我的,我说了算’的心态。当你跟朋友们一起玩的时候,士兵是你们大家的。”
“即便我们扮演敌对方?”
“是的。当比利和阿尔回家吃晚饭,你把士兵收进玩具盒之后——”
“是军用手提箱!”
“对,军用手提箱。当你把它们收拾好之后,它们又是你的了。待人不善的方式有千万种,等你长大就知道了,但我觉得所有不好的行为都源自最根本的自私。孩子,跟我保证你将来不会做个自私的人。”
我做了保证,但我还是不乐意让比利和阿尔获胜。
1962年10月的那天,全世界命悬一线,全看那名叫古巴的热带一隅,我一个人指挥两边打仗,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我都会赢。平路机早前开过卫理公会路(“弄得石头到处都是。”我爸老这样抱怨),四处都是松土。我拢了好些土,先是堆成一个小土堆,然后是一个小丘,再后来就是一座大山,几乎高到我的膝盖。一开始我想称之为山羊山,但这样似乎太没创意也太无趣了(毕竟真正的山羊山就在12英里之外)。深思熟虑过后,我决定将它命名为骷髅山。我还试着用手指在上面戳出几个像眼睛一样的山洞,不过土太干,戳出来的洞老是塌下去。
“好吧,算啦,”我对军用手提箱里的塑料士兵们说,“世界如此艰难,哪能全如你愿。”这是我爸的口头禅,家里有五个孩子要养,他绝对是有理由信奉这句话的。“就假装这些是山洞吧。”
我把一半儿的部队部署在骷髅山顶上,势力强大。我对迫击炮兵在山上的样子尤其满意。这一支是“德国酸菜”。我把美国军队安排在草坪的边缘。吉普车和卡车都归他们,因为开着车冲上陡坡的阵势一定很帅。有几辆会翻车,这个可以肯定,但至少会有几辆能冲到山顶。然后碾过迫击炮兵,让他们尖叫求饶,但决饶不了他们。
“受死吧,”我喊道,拿着最后几个英勇的美国兵,“希斯莫,下一个就是你!”
我控制着它们保持队形逐排上前,还发出漫画书里机关枪的声音,就在这时,一个阴影笼罩了战场。我抬起头,看到有个人站在那儿。他把午后的太阳挡在身后,留下一个被金色光芒描出的轮廓——一个人形日食。
家里有事儿在忙,周六下午家里老有事儿。安迪和阿康在我们家长长的后院里,跟一帮朋友玩“三人投球六人接”,大叫大笑。克莱尔跟她的几个朋友在自己房间里,用她的公主唱片机放唱片:《火车头》《士兵男孩》《帕利塞兹公园》。车库里还有敲敲打打的声音,特里和老爸在修那辆1951年的福特老爷车,老爸管它叫“公路火箭”,或叫“那个项目”。有一次我听他管它叫“那坨屎”,如获至宝,这个词我沿用至今。如果你急需改善心情,就找样东西,骂它是“一坨屎”,通常很管用。
家里很热闹,但那一刻,仿佛一切都静了下来。我知道这只是某种记忆失实造成的幻觉(更别提一个手提箱所能承载的黑色联想),但那段记忆非常深刻。突然后院孩子们的大呼小叫消失了,楼上的唱片停了,车库里也没有敲敲打打了。连一声鸟叫都没有。
那个人弯下腰来,西斜的太阳从他肩上刺入我的眼睛,我一时间什么都看不见,于是举起手来遮住眼睛。
“对不起,对不起。”他边说边挪步一旁,好让我看他的时候不用正对太阳。他上身穿着一件黑色的教会用夹克和一件黑色缺口领衬衫,下身穿着一条蓝色牛仔裤,还有一双磨旧的休闲皮鞋,看上去就像他同时想做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六岁的时候,我把成年人归入三类:年轻人、大人和老人。这个家伙归入年轻人。他手撑着膝盖,以便端详对战中的部队。
“你是谁?”我问道。
“查尔斯·雅各布斯。”这名字似曾相识。他伸出了手。我立刻跟他握了握手,虽然才六岁,我还是有教养的。我们全家的孩子都这样。爸妈在这方面是不遗余力的。
“你的领子上为什么有个孔?”
“因为我是个牧师。等你以后星期日做礼拜的时候就能看到我了。如果你周四晚上去卫理公会青少年团契的话,也会看到我。”
“我们以前的牧师是拉图雷先生,”我说道,“不过他死了。”
“我知道。很抱歉。”
“不过没关系,妈妈说他死前没受折磨,直接上了天堂。不过他不穿你这种领子。”
“那是因为比尔·拉图雷是个非神职布道者。也就是说,类似于志愿者。没有其他人去打理,但他却一直保持教堂开放。真是个好人。”
“我猜我爸认识你,”我说,“他是教堂的几个执事之一。他得收集募款,不过是跟其他执事轮流来。”
“分享是好事。”雅各布斯边说边在我身旁跪下来。
“你是要祷告吗?”这让我有点儿警惕。祷告是在教堂和卫理公会青少年团契里做的,我的哥哥和姐姐管团契叫周四补习班。雅各布斯先生重新恢复团契的时候,是我参加团契的第一年,也是我读正规学校第一年。“如果你想找我爸,他正跟特里在车库里。他们正在给‘公路火箭’装新的离合器。至少我爸是在装离合器。特里主要是负责给他递工具和在一旁看。他八岁,我六岁。我妈可能在房子后廊,看别人在玩‘三人投球六人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