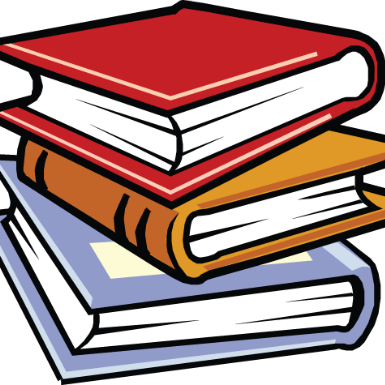而且瞎爷爷说我家请这位阴阳先生绝对是满族人,或者跟满族先生学的手艺,因为他一切的手法都是满族人所用的手法。
再说放完七个硬币之后,就把姥爷的尸体抬了出来,抬姥爷出来的时候先生给姥爷盖上了遮面纸,由大舅抬头,小舅抬脚,其他舅舅在一旁帮衬着,尸体不能走门,因为门是给活人走的,所以只能打开了南窗从窗户里抬了出来,装入了棺材,这才叫入殓。
入殓完毕,在棺材头摆上供桌,上有白蜡烛一对,长明灯一盏,香炉一个,鱼一碗,肉一碗,倒头饭一碗,筷子三双,酒三杯,小贡馒头一摞五个两摞,棺材尾也放着一盏长明灯。
摆完贡品在供桌前放一泥瓦盆,儿女开始烧三斤六两纸。
这三斤六两纸烧完之后,把纸灰打包,放到棺材里,据说这三斤六两纸是留着给生魂上路后大发黄泉路上拦路小鬼所用。
不过我想姥爷是用不上了,有瞎爷爷在谁敢拦路。
帮忙的人在门口高高的挂起了大幡,洋洋洒洒的一串黄纸随着风飘舞着,仿佛在替姥爷的死感到惋惜。
看到大幡挂起,起来吊唁帮忙的人开始陆陆续续的来了。
主持先生又拿了一节木棍和几个小馒头放到了姥爷手中,称之为打狗棒和打狗干粮。
打狗棒据说是死者在下面前往酆都的时候途中路过恶狗地,打狗棒就是给死者留着打这些恶狗的。
而打狗干粮的用处更是大得很,据说途中还有蝎子洞、蚍蜉山、老鼠窟、恶狼谷等,到时候撒放此粮食或麦麸子使这些毒虫、恶蚁只顾抢食东西,就顾不上为难鬼魂了。
一切准备妥当,雇来的吹儿就开始呜呜哇哇的吹起了喇叭,凄凉刺耳的喇叭声响起,子孙跪着棺材两旁,来宾给死者磕头,家属便磕头还礼。
妈妈和大姨已经顾不上哭姥爷了,据说姥姥被推回去之后,一滴眼泪也没掉,就那么默默的坐着,好像回忆起来什么一般,一会微笑一会难过。
妈妈和大姨只能呆在姥姥身边,不停的劝慰老人家。
我和二雷子一直跪在姥爷的棺材旁边,我已经哭不出来了,眼睛红红的肿的只剩下一条细细的缝。
火盆里的纸不停的烧着,姥爷的几个老哥们也在家人的搀扶下来了,一个个泪流满面的跪在棺材前对姥爷嘟囔着心里话。
姥爷是下午死的,按照习俗小三天出殡,出殡的前一天晚上,子孙在先生的带领下烧纸扎,在一片大火中,先生大声念起了《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阗鬼火,春院闭天黑。
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疠自辟易。
哀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存,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懂姥爷的死和正气歌有什么关系,问过瞎爷爷,瞎爷爷也说不上来到底为什么要念这个。
后来想,可能是这先生感叹姥爷的一生正直一时由感而发吧。
忙活了三天,姥爷出殡了,出殡的当天,大舅摔盆指路,浩浩荡荡的车队便开向了坟地。
那时候只有遥远的市里有火葬场,因为我们这地处偏远,所以是可以土葬的,四批高头大马拉着马车,马车上是姥爷的大红棺材。
大约有二十几台车排成一排,遇桥撒纸钱,遇路口也撒纸钱,到了坟地先生敲打了几下领魂鸡,家属象征性的撒上一把土,众人便开始埋了起来。
到此姥爷的葬礼彻底结束,一直到回家我都没有喝酒,我怕,我怕瞎爷爷跟我告别,我怕,我怕看见姥爷那对人世间的眷恋。
姥姥依然不说话,仿佛身边的一切都和她无关一样,就那么静静的坐着,怀念着。
看着日渐消瘦的姥姥,我轻轻的趴在了她身上。
姥姥抚摸着我的脑袋良久轻轻的说道:晓南,你能看到你姥爷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难道姥姥知道我能看见那些东西?
却听姥姥叹了口气说道:你一定看不见,可我却能看见,你姥爷始终在我面前,他一直向我招手,我知道他一定很孤单,一辈子,一辈子我们都没离开过,现在他却先走了。
姥姥像讲故事一样,讲起了她和姥爷的过往。
在我心里一直认为姥爷和姥姥和许多那些年的夫妻一样,对付着过着日子,根本没有什么感情可言,有的也许就是这么多年在一起的亲情。
可今天我才知道我错了,虽然他们没说过,但他们一直都是那么的爱着对方,姥姥讲起姥爷的时候脸上洋溢着浓浓的幸福让我都跟着感觉到了浓浓的爱意。
可现在姥爷却先走了,撇下了姥姥一个人孤独的留在世上。
最后我只记得姥姥不停的重复着:别着急走远,等等我,我就要下去找你了。
第九十九章 集市风波
时间的脚步就像赛跑中的乌龟,看似很慢可一个不注意却已经跑出了很远,一转眼一年多过去了。
生猪的价格一路暴跌,父母辛苦建成的酒厂终于负债累累的倒闭了。
整整一年,我滴酒不沾,从黄纠纠的表情和动作中,我能感觉到黄尖尖还是会偶尔回来看我。
虽然我也很想它,虽然在睡觉时耳边会感觉到它的声音,可我依然没有再粘一滴酒,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血降的事我没有再继续查下去,而我这一年也相当平静,干吧男和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来找我麻烦,这让我真正的舒爽了一下。
一年里我享受了一个孩子该做的和该玩的事,没有灵异,没有鬼怪,生活如此的轻松惬意,即使家境一天不如一天,我还是依然快乐的生活着。